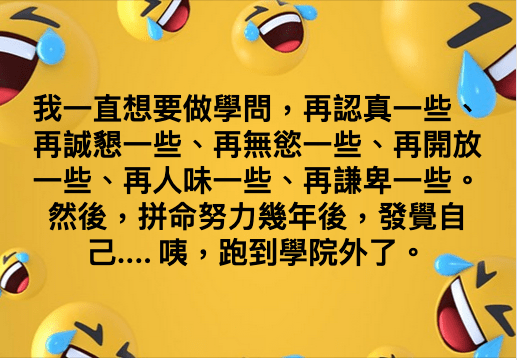至於這個病從何時開始感染的?到底該往前推到那個時點去檢視這個學問的叉路口?我自己比較prefer從Grand Theory與其左翼反撲切開,這個左裡頭有兩個交織的線索,一個是left-grand(比較落實經驗研究的支線是歷史社會學的回返,Tilly, Skocpol, Wallerstein…); 另一個當然是後學的某種「新左」。我是認為,社會學可惜的是從grand-right變成grand-left,但整個micro-sociology被丟棄了。
拿經濟社會學史來回顧,基本上整個站到rational choice的對立面去,network analysis有一定階段的對話成績但單薄,但我們越來越自己關起來玩爽的時候,人家整個非主流經濟學超乎rational choice做了非常豐富多產從micro-level的修正,社會學(連經濟社會學的主流)在內都整個忽視它們的發展(Fred Block是個異數,win my respect),這個內部成熟建制的僵化造成實質上越來越失去整個學問的活力,我自己也是因此而漸漸脫離越來越呆滯、讓人無法忍受的經濟社會學。
我在離開經濟社會學的同時,另外一些從micro出發的社會學小/非傳統吸引我的注意,譬如ethnomethodology(還有phenomenology,這個未來中興社會學的命脈比較幽微有空再談) ,它一度是grand-right的(好啦,就Parsons)的反對派,但他非常marginal,幾乎在社會學裡消失,從他用ethno-methodolgy來取代sociology就知道命運。社會學者感興趣的是Goffman(而且果如所料,集中關注在「污名化」這樣單一主題的粗糙理解,接著就被消化變成「區別歧視論」的養分)。老天有眼,這個徹底反對grand abstraction的社會學資產,我覺得被Latour在加州實驗室的田野所承接,延續一絲未來回返光榮的契機。
但幾乎可以預料地,在STS內部的重大爭議與Latour的退出(拿掉social,然後跟建構論保持距離)中再度宿命般地重演了一次「脫社會學」的決裂,「建構論」這個曖昧的概念以及其主流的版本也成為了「區別歧視論」的又一個養分。你看這隻思想病毒一路吃掉「宿主」多少的營養體力,最後還直接take over大腦!
社會學過去20年間不是沒有從micro抵抗abstraction(或Latour的警語don’t jump)的在野派,我自己也是從這裡開始DxS尺度問題的自問、自我發配邊疆的放逐、與自我改造的長征,現在也到了一個裡外不是人,不知道該不該直接「脱社會學」,還是該稱呼自己是「另類社會學」的尷尬位置。總之,微視社會學基礎的腐蝕流失是一個社會學很難短期內填補的重大損失,正為此而付出慘痛羞辱式的代價。
我寫多了,這只是我回應朋友「發瘋」試圖檢討自省的第一條回顧線索。其他還有好幾條有空再來自言自語。
譬如,第二,我覺得社會學已經失去自己作為一門「綜合科學」該守住的戰略與學科血氣,我們學科建制化後長期偏安在「社會(建構論)」這個概念的角落捨棄了跟其他學科,經濟學、心理學、甚至認知神經學、生態歷史學的交際混搭、吸納轉化它們的知識發展為己用的原本學科體質,變得抓著一些已成cliche的思考填充物在學科分治下的系所獨立王國內部自嗨,培養一些莫名其妙傲慢的憤青與不認真追根究底突破學問的安逸,擺姿態變成在做學問,道德掛帥當成self-righteous的自滿。
第三個被社會學踢出去的養分,然後因此造成他現在的貧血症與多樣性喪盡,跟時代對話的氣力消散,當然我一定要加上對於objects的輕視。啊啊….再寫下去就寫不完了。我真的衷心希望,社會學可以跟著這次病毒瘟疫一起毀棄重生,那些散置在各個角落的marginal力量可以在這場災難後的廢墟重新開啟對話,再次集結,讓Sociology great again!